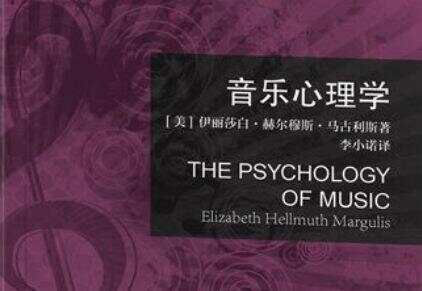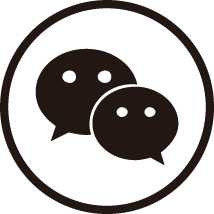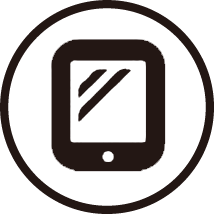文化的本质在于传承,而决定文化特性的因素,却非人力所能致。即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日,许多被自诩为人类创造的奇迹,其实无不仰赖于物理环境与工具,人的实践与控制及认识自我的能力,很难说相对于古人,有质的飞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自近代早期以来,知识创新的速度日新月异、迅速产业化,并与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城市文化流通体制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交互作用。现代大学中以知识生产为主要目的专业分科,也仿佛工业革命时车间林立、生产线如织的工厂。知识分子则俨然产业工人。由于分工的日趋细化、门类的壁垒丛生,知识生产者每每被自己的产品所异化;而社会其他人士对于知识的汲取与运用(无论旧说还是新知)则很难逾出消费经济的窠臼。与此同时,古人在求知与传授时所念兹在兹的修齐治平及文脉道统,却愈来愈模糊。当工具日益延伸与“优化”人的实践之时,知识就越来越远离这种实践,甚至变成人类活动中的一种冗余渣滓。在此情形下,人文通识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意义,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正所谓“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学而时习之,不仅不亦乐乎,而且像身体所需的基本营养,变得性命攸关。上海音乐出版社此次引进“牛津音乐人文读本丛书”,其义亦大矣。
通识并非浅显的学问,就如同常识其实比新知具有更本质的意味。古人常有“布帛珠玉”之喻,以明对个体(也包括由个体构成的团体,由团体组成的社会)而言,朴素平白的日常衣食一般的“通识”,比奇技淫巧甚至曲高和寡、示人以秘的珠玉般的“绝学”更为紧要。而且,人们常常会因为求新求变而忘本,故而“通识”就需要经常被提起,需要更加意地去传承。我们说人体营养要均衡,就不能只摄取一种食物,健康阅读也是由各种内容构成。须知:只有在一定的广度之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才会有深度,个体的实践才有沟通“天人”的意义,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才能和谐共洽。而对任何精微“绝学”的探索,最终也必将反诸于本,犹如百川归海,否则必将中途枯竭、自绝于世。《易经》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学问的最高境地与学者的最高追求,便是让绝学成为常识。
中国古代的学术和艺术,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了不起的“创新”,但在当时创造者的主观认识上,只是复古。对于古人而言,不顾既有的传统与规训的创造,只能导致精神的堕落。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所叹“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同理,西方文明的源头——欧洲中世纪也具有一种对于新事物的恐惧,对变化极为敏感的伟大历史家吉尔伯特·德·诺让(1053-1124)对1111年琅城市民为了反对主教而创造了被称为“公社”的组织,不禁痛斥“这个最坏的新字眼”(“Communion novum ac pessimum nomen”)!直至“法国大革命之后,创新才开始被广泛用于正面含义。”而前现代社会这种厚古薄今的认识的观念前提,在于对古老传统(包括神意、圣学与先贤的遗教)的尊重和对人把握自身及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的深深怀疑。这种谦逊的品格无疑与人本主义的迷思及人定胜天的妄念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外,人类的大多数人文精神遗产,都是在前现代文明中产生的。对各代历史的深入理解,使我们不难感到:对“进步”的渴望其实是一种近乎动物性的低级本能,而进步本身就如同衰老一样无法躲避;人的智慧的极限,止于某种经验式的不可知论。诚如陶渊明所云:“好读书不求甚解”,对过分背离常识与社会实践的、钻牛角尖的求知欲的抑制,就像压抑面对金钱和色欲时的贪念一般,也构成了一种与启蒙主义和现代性相对立的伦理及美学。
在古典价值体系中,不以创新获利为目的知识传承,却更能培养出城邦(国家)的实际领导者与生产斗争的实践者,并以他们敬天法古的人生,反过来丰富承载着这种价值的常识性经典。所谓: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
而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人为“人所创造的知识”所蒙蔽,几乎成为一种流行慢性病。许多被现代人视为当然与必须的观念结构——尤其是建立在“重估一切价值”、以科学和理性为外挂、梦想“解放”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现代价值体系——以知识的名义愚弄着民众,造成了一大批受过教育的群氓。热衷于概念和系统的“配制式的”新教育的荒谬与虚弱,与各种古典文明所共有的“启发式”老教育是势不两立的。比如饱受现代知识阶层提出的“普世价值”解构的“爱国”的古代伦理,当然是人文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
在古罗马,当父亲告诉儿子为国捐躯乃甘美而合宜之事,父亲对自己的话坚信不疑。他在给儿子分享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为他本人所共享。而且他也相信,这一情感合乎他的判断力在高贵死亡中所体认的价值。(C.S.刘易斯:《人之废》)
贺拉斯的诗句“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用孔子的话来说,便是“鲁人欲勿殇重汪踦,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就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道之体原,无分东西,其所用有不同耳。东海有圣人,西海亦有圣人,此心此理原是攸同。然而曾几何时,在启蒙主义语境与现代性价值系统中,一度为“轴心突破”以来的东西方圣人共识各表的“道”已经沦丧为各种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了。以开启民智自视的知识分子中的“守道者”,所守者,不过道之沦丧。而各种光谱式汇聚的左、右之争,都是“propaganda”(宣传),而非“propagation”(传承),正如孟子辟杨、墨之邪说:无论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还是粉身为齑而不惜,与夫子叹为不可得的中庸相较,其实为一。对于各种对立的现代价值系统,无法择一而从,只能从整体上予以决然之超克。
故而,人文通识教育包含的“义理”是与知识对人的异化相对立的。广泛的通识式求知,本身就是一种解弊,是对于知识分工过于细密、知识阶层越来越职业化、知识生产越来越远离个人实践与人格完善的现代性症候的解药。当读者(包括暂时离开了知识生产线、回归读者初心的知识分子)透过对承载着古典价值观念和前人经验感悟的人文通识的把握,祛除概念化的紧箍之际,“庸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丸,而使之浮游尘埃之外耶?”(元人赵文语)。早在18世纪——所谓的“启蒙时代”,当一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的真理,可以取代教会和君主,用现代知识体系来取代宗教之时,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卢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但愿一流的读书人在君主们的宫廷中找到体面的庇护所吧,但愿他们在那里得到与自己相称的唯一报酬,这可是他们做出贡献的报酬啊,因为,他们把智慧传授给人民,增进了人民的幸福。【……】不过,只要权力独处一边,光明和智慧独处另一边,读书人就会很少想到伟大的事情,君主们就会更少做出美好的事情,而人民就会继续卑劣、败坏和不幸。(卢梭:《论科学和文艺》,刘小枫编,刘小枫、冬一、龙卓婷译)
孔子云:“学也,禄在其中矣”。圣人的教训与卢梭的这段话,可谓古今同符。人文知识的源头活水,正是支持人类社会运行的体制(institution),真正的“读书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现实环境。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人文通识教育的开展,绝不是为了培养象牙塔中的章句之徒或精致高蹈的利己个体,而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项事业培育优秀的实践者。那么,我们译介这套在英语世界久负盛名的丛书读本的起意,便在于立足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本位,借鉴欧美“人文通识教育”的经验,用夏变夷,师其长技,最终使域外经验中的古典价值溶入我们自身的观念结构中。王德峰教授论及中西文化不同之由来,有一段话对今日读书界颇有深省:
中国人的生命实践是汉语的实践。汉语与欧洲语言有根本性质的差别,因此,中国的生命实践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生命实践,即使在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时代,事情仍然如此。
汉语是中国人存在的家。中国人以汉语之家为家。中国人对世界的经验,是汉语的经验。只要汉语仍然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就总在汉语中形成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也在汉语中形成我们基本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态度。因此,在汉语中,即在中国思想和中国情感中。(王德峰:《中西文化差异之渊源》)
而刘小枫和甘阳这两位对西方文化有着深邃理解的当代思想家,在《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014)一文中的一段话,更犹如韩愈《原道》,可谓对沉溺于启蒙主义和现代性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棒喝:
但我们历来强调,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研究是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学界尤其人文社科的真正国际视野和文明使命,是以母语思考写作的深度海纳百川地整合中西思想资源,从而最大程度地发展中文思想学术文化……一个文明的根基和灵魂乃在其语言文字,中文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首在“中文的主体性”,离开了中文,还有什么中国文明?还有什么中国主体性?还能“构建”什么“中国文化主体性”?
在“主体性”的意义上讲,对作为文化现象和文明标志的所谓“西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在人文通识教育的论域中,也就绝不仅仅是为了训练专业技能和填补所谓理论空白,而是着眼于某种形而上的志趣。这种关注,既包括对作为中世纪以来从西欧天主教文化直到冷战后最终形成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谱系的深度了解,也包括对当下欧美知识界和思想界对人类音乐活动的观察与深思的分析,并最终基于自身的本位立场,以批判的眼光更深刻地理解这种异物,当这种理解渗入未来中国人建设自身文化的实践中的时候,具有中国风格与气派的音乐文化,便是被借鉴的西方音乐的回馈与重塑。
相较于别的知识门类,音乐最大的不同,恐怕在于其实践性与实用性。尽管可以趋身于最精微、抽象与智性的境地,但音乐的存在之所以对人具有意义,却在于它的感性、日常与实用。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音乐最容易于脱离常识,又最不得不依附于常识。音乐的“伟大性”必须建基于某种琐碎、庸俗和平凡的重复之中。这使得音乐学家们必须随时在两个极端之间平衡与反思。而当下我国的音乐学术(尤其是高校中所谓的专业),就总体而言,越来越呈现出繁琐的经院式色彩和脱离实际音乐生活的倾向,究其所原,恐怕在于在吸收西学中相关内涵的过程中“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英国哲学家阿伦·瑞德莱以“烹调学”而非“营养学”的哲学方式来思考和研究音乐,作者在叙述自己曾经被汉斯力克所影响时写道:
所以,我决定不仅把音乐同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而且把它同歌唱、舞蹈、进行曲以及一切不可被看作“纯粹和绝对音乐”的东西分割开来。通过这种方式,我满怀信心地期待音乐在摆脱了一切玷污了它的影响之后,把自己的秘密展示出来。但这秘密始终未曾展示,而我却情愿把这种情况归诸自己的无能。更令我苦恼的是,别人正在达到的某些东西,在我看来却总是不可信的。一旦我自己注意到这一点并为之困扰时,整个探索之路就成为可疑的了。归根到底,在许多音乐哲学的研究方式中有一种古怪的东西。试图把音乐整个地孤立起来,硬要去清除音乐本身所具有的语境关联——实际上也是在清除我们接受音乐时的语境关联——这就好像是把音乐假定为火星来客:它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书桌上,不知来自何方;它形式完美,却整个地是一个神秘现象,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这就是我所说的古怪东西,它展示了一幅远离真相的图景。(阿伦·瑞德莱《音乐哲学》,王德峰等译)
瑞德莱像在竹林里格物致知却得了重感冒的王阳明,说出了我们都曾经面对、但却无人指出那是皇帝的新衣时的困惑;而且,汉斯力克的《论音乐的美》中对“纯音乐”所下的定义,实际是一种音乐中的种族主义,是布尔乔亚文化在没落之际的一种精心设计的话术,本来不值得一驳:对音乐形式本身的解析属于音乐理论学科,而对音乐作品或乐曲如何在语境关联中展示出某种意义,则是基于常识的求知。那种将音乐(尤其是自以为高雅的古典音乐)过度包装、故作神秘、玄乎其玄的文人伎俩竟然一度得到了那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可谓“甚矣,中国之无人”!如果音乐哲学的目的是拒绝使大多数聆听者清晰地理解音乐,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但如果音乐已经被清晰地理解了,那么音乐分析家和历史家似乎也就无需借助哲学的工具了。音乐学和哲学一样,在当今都面临这样的困境:所能耕耘的领地越来越小,而且地力越来越薄。唯一的出路,是不断回归常识。而对日常经验的漠视,恰恰是音乐学科体系不断划分后出现的致命问题。
音乐学(及音乐哲学)如果能像瑞德莱所期待的那样,回归日常经验(尽管这要冒着在学理性上自我消解的危险)与文化事实,那么即使像维特根斯坦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日光下的雪人,至少也是为音乐学家们起到了“观念解蔽”的关键作用。这样的学问虽死亦荣。在音乐学的诸学科中,也许只有音乐哲学家们是以消解自身的学科为最终目的一群人,他们就如同清道夫一样,为我们去除在实证性研究和分科越来越细的理论性思考中堆积起来的垃圾和冗余,使我们透过理性与感受的互相作用(复杂的现实和研究实践往往会使这种作用过程变得难以把握),不断回归到某种自然、原初与本真的状态。如果,音乐哲学真有自我消解的那一天,也就意味着哲学精神被灌注到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分支之中。
换一个视角,哲学家们必须解决悖论;而历史学家们则欢迎之。历史学的任务,是发现、理解和呈现这种矛盾,并且试图将它们置于其所产生的语境中去解释其成因、观察其影响。音乐上的种族主义既然不是天外来客,那么就是历史形成的产物。从方法论上讲,“科学主义”是形式主义音乐观念的基础:
科学主义是一种信念,即凡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标准,也同样适合于每一种其他类型的研究。这一信念乃是一个谬误。(阿伦·瑞德莱《音乐哲学》,王德峰等译)
这之所以是谬误,无非是由于它产生于19世纪:既是科学昌明、理性发达的时代,又是迷信泛滥、主观至上的时代。资产阶级将浪漫主义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结合(我们绝不能忽视这给音乐这一公共艺术带来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对人类所造成的震撼),就得出了瓦尔特·帕特(Walter Pater)“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的论断。一方面越是冒用科学主义的名义将音乐画地为牢、标榜为界定清晰的科学,一方面越是以先验的名义去看待音乐和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的、永恒真理的世界”。谢林的理论(艺术的这种能力起源于人类超越认识领域的能力:“没有任何审美的材料比声音更适于表达不可言说者”)把艺术绝对化了,用来取代被启蒙主义动摇和被法国大革命摧毁的宗教与道德。这样,我们从“解蔽”的目的出发而进行的音乐人文读本的引介,便又回到了理解“古今之变”并在其中寻求一个适合自身的立场这一根本出发点了。
无论是《早期音乐》还是《音乐心理学》、《管弦乐队》还是《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学》还是《布鲁斯》,都将为我们的读者将过去在“学术语境”中经常孤立而贫乏化的“音乐同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在这一系列的有关音乐人文的小书中,有一本《乡村音乐》特别使人着迷,因为它呈现出一个音乐上完全“非西方”的、疏离了现代性的美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朴素谦逊的亲切力量:
乡村音乐常被打上山野人、乡巴佬、土包子、大老粗、种族主义者的烙印,它是美国各种流行音乐风格的可怜继子,不像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剧金曲和灵魂乐、摇滚和说唱那样思想深刻或新潮时尚。然而,对唱片销售量更为准确的计量方法出现之后,人们立刻明白,就单纯的数据统计而言,乡村音乐才是一切音乐风格中最“流行”的那个。而且这种音乐的生命力倔强持久,正如最杰出的乡村音乐家们似乎从不隐退。乡村音乐虽然偶尔浮现于美国国民意识的顶端,但正是乡村自身根深蒂固、几近隐秘于地下的本性,才使乡村音乐在许多方面成为美国最深刻的本土流行音乐。
……
我们可以将乡村音乐想象为一条河流:发源于多种音乐文化之间独具美国特色的联姻,蜿蜒流经不同的地区,时不时地偏折改道,但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归正轨。所以这本小书无意于“定义”乡村音乐,而是沿着这条河流小心求索,不时地下水尝试,寻找共性与差异,对论述稍作扩展以涵盖最受喜爱的风格和表演者,力图成为一名值得信任的向导。你可能不同意本书所走的路线,或反对我们一路选择的站点——那么请随意偏离路线,踏上自行探索的征途。乡村音乐足够海纳百川,可以包容众多不同观点。(理查德·卡林:《乡村音乐》,刘丹霓译)
在面对根本性的问题时,决定深度的还是广度,而对未知不懈的追索,总是依永恒的循环而折中。这正是通识教育的另一种意义:使我们在既有的常规系统之外,获得实实在在的新知,却不会被导入莫测高深的歧途。当我们环游世界之后再回到出发之地,最终得到启示的是对后者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