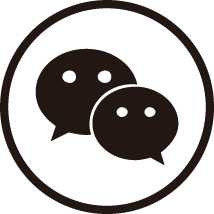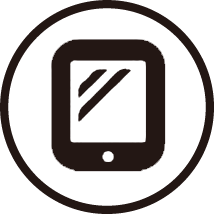摘要:三十年来,作者与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学界的不断交往,通过小溪汇河海,润雨细无声的路径,融铸了自己由南而北,由内向外,从中国至周边走向全球的整体艺术观和世界文化观。且经由远眺到环视,再到实际操演的过程,完成了自己涉足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教学的经历和体验。文章结合历次参加中韩、中日音乐学术研讨会,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学术研讨会和指导研究东北、东北亚音乐博士、硕士论文的经历和体验,讨论了相关的研究现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趋向的展望。
关键词:东北少数民族;跨界族群;研究现状;存在问题;未来趋向
中图分类号:J6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2)01-0044-08

杨民康,哲学博士,云南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音乐学院学术期刊《北方音乐》于2022年度改版创刊,这是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即将问世的又一本重要音乐学术刊物,也是音乐期刊界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盛举!可喜可贺!2021年5月末,我荣幸地接到刊物创刊号的约稿信,田可文副主编嘱我:“请谈谈你的跨界研究问题,可以涉及东北亚的跨界(音乐研究)”。鉴于笔者自入职以来,与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一直不间断地有过交集,同时我们近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会牵涉到这个领域范围,故此笔者接下了这个任务,本文即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撰写本文时,掐指一算,距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北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1],恰好有三十年了。回眸我在此时期内与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学界的不断交往,通过小溪汇河海,润雨细无声的路径,融铸了自己由南而北,由内向外,从中国至周边走向全球的整体艺术观和世界文化观。且经由远眺到环视,再到实际操演的过程,完成了自己涉足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教学的经历和体验。这时,适逢我们正与《民族艺术研究》学刊相约,由我方集体编撰“田联韬先生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术专题。所以,这三十年“涉北”音乐研究经历,或许也可以搭上这趟正在驰驶的列车,将之纳入这个微观学术史专题范畴予以讨论。
一、远眺北境——从处女作《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在吉林出版说起
我作为云南籍学者,多年来主要从事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接触,主要是维系于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科方法论建构与相关的研究生教学。而从时间上看,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学术际遇,则让我开始与东北少数民族暨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结下了不解情缘。
我们的第一次学术际遇发生在1991年,我刚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不久。这时的中国人文社科出版界,挟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余温,频频亮招,四面出击,积极地向国内中青年学者征求富含文化底蕴的学术选题。这时,正在艺术研究院读博的好友、《中华艺术文库》主编之一杨晓鲁找到了我,告知吉林教育出版社正在筹划的这个项目,意在通过将不同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或体裁)与相应的社会侧面(或现象)结合起来,为当时心灵糙动,渴求新知的青年学生打造一套融社科知识和学术理论为一体的多卷本艺术文化丛书。当时刚结束田野考察和学位论文写作,初涉学术殿堂和文化讲坛的我,不禁为之怦然心动,于是便根据自己此前通过阅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初步思考了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经历,草拟了《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这个选题,并且得到了主编和出版社编辑刘丛星先生的首肯。此书出版后,得到业内外读者的诸多鼓励,1994年获得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可以说是我入行以来最为珍视的学术荣誉之一。不仅因为它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奖,更是由于评审专家来自首都北京的人文社科不同专业,少有如今日益常见、让人窒息的文人相轻和业内歧视,并且在当时这几乎是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唯一人文社科奖项。事隔多年后,还有不少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朋友见到我,就会提到此书。著名学者、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教授也在初版十七年后,还记得这本小书,并慷慨地予以重版。所以我想补说一句感言:谢谢东北!谢谢吉林教育出版社!是你们当年的睿智和大度,宽容与接纳,让我提振信念,沉入学海遨游半生并沉浮至今!
第二个际遇是1992年8月,我应邀前往辽宁抚顺参加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布朗族音乐史》,会后由会议安排赴新宾考察满族音乐文化,一下车就看到满街的东北大秧歌表演迎宾队伍。在新宾考察期间又对满族萨满音乐和满族秧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前于1990年,我曾经参加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该年又来到抚顺市参加是次年会,次年(1992年12月),我又随同乃师田联韬教授参加了西藏山南地区的中国西藏第二届雅砻文化节,再加上这一时期比较频繁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考察活动,一系列由南至北的音乐文化考察经历,让我又有了新的学术冲动,催生了自己的第二部传统音乐学术著作《中国民间歌舞音乐》[2]。在这部新书里,我较之于第一部书,能够更有底气地去讨论中国民间歌舞音乐的“整体性(跨区域性)——区域性”风格格局(绪论至第四章);能够更好地把握北方汉族秧歌的“共性”舞(乐)种与“衍生”舞(乐)种的关系(第四章);能够更加准确地解释北方多民族歌舞乐系中萨满歌舞的风格特点(第九章);还能够提供相对完整的北方民族歌舞音乐表演的图片(修订版)和谱例。这些,都与历年来旁涉北方民族音乐文化考察的经历分不开。
二、环视诸亚——中日、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拓宽了我的眼界
到了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前十年,我们开始涉入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课题。这一时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含少数民族音乐)学科方向及我本人与东北及东北亚音乐研究的关系逐渐密切。在两校之间许多相关的学术交往中,尤其可以称道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2003年开始,由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研究中心与韩国音乐学界共同发起,长年保持每一两年一届,轮流互访的“中韩(韩中)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从2008年第四届开始改名为“东北亚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第五届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寺召开),2012年第七届开始又改为“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至今已历九届学术会议。另一个是近十余年来逐渐开展起来,包括东北与东北亚在内的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项目,如今也产生了许多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学术会议。
若从地缘关系上看,中国东北与韩国、日本同属东北亚和东亚,笔者相继参加过的中日音乐比较国际研讨会和中韩(韩中)佛教音乐比较国际研讨会两个学术会议系列,均与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若从两类会议发起的时间看,前者的产生在先,主要为中国的福建、上海等地学者发起;后者稍后产生,主要由北京与韩国学者发起。尽管韩国和日本都属于东北亚,但在研究对象和讨论的问题上各有专属,参会人员也不尽相同。所幸的是,笔者作为北京学者,不仅同时参与了两个系列,此外还参加了由台湾学者发起的,有日、韩、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参与的“佛教东传20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的参会论文也同样涉及了东北亚地区中国、韩国、朝鲜跨界族群佛教音乐的课题研究问题。参加了上述学术会议并与中外学者展开较频繁的学术交流之后,对于本人所涉及的南方和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佛教音乐研究及树立中外佛教音乐乃至跨界族群音乐的整体全局观皆有很大的帮助。
(一)通过台北、日本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东北亚音乐结下渊源
在讨论中韩(或东北亚)佛教音乐比较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提及此前参加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1999年,我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已经针对云南傣族、布朗族的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田野考察。2002年完成的学位论文,即以西双版纳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3]。2000年10月,我在田青老师引荐下,应邀参加了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和台北南华大学召开的“佛教东传20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论云南少数民族南传佛教的乐器、器乐音乐及其与原始佛教音乐的渊源关系》[4],同时还第一次聆听了日本和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佛教音乐与东亚、东南亚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次年(2001年)12月,我又应邀参加了日本冲绳召开的第4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宣读了参会论文《论佛教传播史晚期的音乐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乐的比较》[5]。文中,我结合应用了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搜集的中外研究资料和前一年在台湾佛教会议上韩国和日本学者发表的观点和看法,讨论了早期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佛教音乐文化交流及其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同异关系。在后一类资料来源中,日本学者中西和夫《日本净土教仪礼的音乐特性》[6]一文里介绍了公元9世纪初日僧空海与最澄到唐朝留学,所带回的唐朝新兴佛教佛法和仪轨,奠定了日本佛教文化“正统”的思想基础。其中所含有的仪式音乐内容,成为日本现存的各派声明之源流。最澄在比叡山开创天台宗,其仪式音乐、声明由圆仁法师集大成,在比叡山与京都大原的佛教传统中延传下来。在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下称《入唐记》)[7]中,以外来求法者的眼光,目睹并详录了当时中国佛教所用的大约八个佛教法会仪式的仪轨,其中包括扬州开元寺的天台大师忌日仪式、敬宗国忌日仪式、四十二贤圣供奉仪式,赤山法华院的新罗讲经仪式、一日讲式与诵经仪式,五台山竹林寺的设斋礼式及七十二贤圣供奉仪式等。由于古代的朝鲜是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中转站,所以日本佛教界也一向颇注意朝鲜佛教文化的发展动态。在《入唐记》里,圆仁提及当时位于山东的赤山法华院里,约有客居唐朝的新罗僧侣40余人。其所有讲经礼忏仪式,除黄昏、清晨二时礼忏外,皆依新罗风俗,主要按新罗语音进行。在诵经方式上,已有领诵加齐诵、一领众和与对诵等类。在经腔里用的语音和旋律上,凡一人领唱,属偈颂性质的梵呗皆使用中国旋律(唐声),如“称叹佛名”等众人齐唱(大众同音)的梵呗,就采用新罗风格的旋律来唱。据此,2000年台湾佛教学术研讨会上,有韩国学者比较当时中国佛教音乐的情况认为,“例如在中国,虽然一边有印度风的梵呗,一边新作了中国式的鱼山梵呗;在韩国,受用于中国式的梵呗,一边新作了韩国式的梵呗”。[8]根据对上述史料和学者论点的比较分析,我在论文中继而论述道:“在与本土信仰的相互关系上,中、日、韩等国的北传佛教均与南传佛教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即前者在大大小小的反复和波折中,始终没有能够像后者那样,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在本国舞台上占据过统治地位。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一方面在‘大传统’的层次范围,佛教只能既同道教等本土宗教分庭抗礼,又同后者及儒家文化发生一定的互渗互融;另一方面在‘大、小传统’的(文化的或社会的)两个层次之间,佛教又同各种带有佛教信仰因素的民间宗教类型分层而立,从而形成大传统(释道儒)和小传统(民间信仰)之间‘多元分层,并立相迭’的发展格局。至于南传佛教,从一般层面上看,在其‘本土’(民族性、地域性的)宗教信仰文化范畴存在一种相对局部性的‘小传统’,而在南传佛教的自身传域(跨民族、地域、国界的)范畴则覆盖着另一种相对整体性的‘大传统’。而从具体的仪式形态来看,不仅属整体性的‘大传统’同本土的或局部的‘小传统’结合得异常紧密,而且二者还呈相迭互融,主次分明的状态。”[9]通过上述学习与讨论过程,我初步涉及并介入了与东北亚佛教音乐相关的研究内容。
(二)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建立起我的整体格局观和“宏观+微观”学术思维
带着世纪之交撰写博士论文和在不同学术研讨会上与中外佛教音乐学者交流的新鲜感受,我从2003年开始,连续参加了一至四届中韩(韩中)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又于2016年5月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九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一共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云南沧源县上班老寨佤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调查报告》(2003,北京)[10]、《论南传佛教傣语经腔的地域—民族性音乐风格及文化特征》(2004,韩国,第二届学术会议)、《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2005,厦门)[11]、《唐代〈骠国乐〉中的十二首佛曲及舞蹈内容解析》(2006,韩国)[12]、《缅甸南传佛教升小和尚仪式中的传统乐队展演研究》[13]。正是在该类会议的“跨界宗教音乐文化研究”主旨引领下,我身携这些涉及不同民族、地区、年代,并含有“由内向外”,由中国少数民族渐及跨界族群意图的佛教音乐学术论文,代表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研究学界参与了中国与周边三大佛教流派音乐文化的学术大讨论。它给我们中国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中青年民族音乐学学者带来的较直接影响,一是通过上述中国与韩、日等国三大佛教流派音乐文化的并置研究和比较研究,让我们建立起了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基础的音乐文化与身份认同观念,以及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音乐文化比较研究课题予以整体把握和宏观比较的研究思维;二是通过跨国会议和相关田野考察过程,实实在在地接触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音乐和文化,让我们日后在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有了底气,为此后进一步开展南方和北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
以我本人的情况为例,在自己所从事20多年跨界族群音乐比较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对于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南传佛教仪式音乐展开的课题耗时较多,花费的精力较大,在此类课题方向中占了较大的比重。虽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个体化、局部性的个案研究课题,但从其研究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的形成过程上看,却是在一直与之交替、循环展开的中韩、中日佛教音乐比较等研究课题相互影响的国际化学术氛围里,受到后者的熏染、培育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尤其其中相继更名为“中韩”(韩中)、“东北亚”和“亚太”的系列性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在中方的袁静芳(领衔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田联韬(领衔少数民族的藏传、蒙传、南传佛教音乐研究),韩方的权五圣、李辅亨等前辈学者的引领及许多中韩音乐学者的参与下,已经从一开始相对单纯的中韩(韩中)音乐比较研究逐渐拓展、升格为一项宏大的中国与周边“汉传、藏传、南传”三大佛教音乐体系的综合性考察和比较研究课题了。就我本人来说,通过对这项研究课题的全程参与,产生并形成了自己以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及“原生、次生、再生”文化层为主的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继而又树立起了包括中国与周边佛教(音乐)文化圈,亚洲各部中、梵两个文字与信仰文化圈互相交织以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多元一体分层格局”在内的整体格局观和“宏观+微观”学术研究思维。
再结合历届中韩(韩中)佛教音乐研讨会的论文发表情况看其与东北、东北亚音乐的关系,可以看到尚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现实性问题:其一,多数论文涉及并讨论了中韩佛教音乐的各自特点,也有一些论文对两国佛教音乐进行了横向比较,但对于中国一侧还仅限于涉及了古代历史上佛教及佛教音乐由山东及东南沿海经海路传入韩国的情况[14];其二,除了在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个别论文,如杨久盛教授在第七届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发表的《千山佛教经韵——兼谈北方经韵与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在韩国举行的“第八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研讨会”上,有辽宁千山龙泉寺寺庙乐团和随团学者参加之外,其他历次会议很少有东北地区的佛教音乐学者参与,且在参会论文中很少涉及当代东北地区的佛教音乐;其三,到了后来,韩国学者将比较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当下和韩国佛教音乐与东北相邻的其他省份,如同属东亚,但位于东北亚地区之外的蒙古族佛教音乐和邻近南亚地区的藏族佛教音乐[15],但是在中韩两国学者中,仍然鲜有对东北与韩国、朝鲜的佛教音乐和其他当代音乐展开跨地域性比较研究。由此而论,这一时期的中韩、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项目还较少涉及东北地区与东北亚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课题。这至少说明了尽管两者的地缘相近,其佛教音乐在早期历史上存在同源共生的文化关系,但却在后世有着不同的传承渊源和传播路径,以致其当下性比较研究课题在当时未能受到学界重视这个基本事实。
三、走向近观——亲身参与东北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教学工作
近20年来,通过更多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学者自身的学术努力,中国北方、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课题和成果不断增加。对我们自己来说,通过历届中韩、中日音乐国际研讨会上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我们一定程度了解了同属东北亚的中国东北与韩国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状况,并且经由对东北及韩国佛教文化的多次实地田野考察,为此后近身参与并指导硕博研究生开展东北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一)参与东北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作为一名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在南方少数民族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但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我的教学工作及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的范围必然会扩展到北方民族与周边东北亚、中亚地区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如前所述,在长达十余年里参加历次以中韩(韩中)、中日佛教音乐比较研究为主旨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自己主持开办多次中国跨界族群音乐学术研讨会的过程中,我通过“远眺”和“环视”,逐渐树立了自己包括南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的连通以及(音乐)文化圈、文化层互相交织、嵌合在内的整体学术格局,铸就了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多元一体分层”文化与身份认同观念。近十余年来又通过与北方学界同仁的学习交流活动,让我达到了“近观”北方少数民族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现实性目的。在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综观和评估之后,又逐渐将其应用于自己近十余年来面对南北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就我而言,较早期的北方院校学术交流活动,是在2004年10月,自己曾应沈阳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及杨久盛教授和林林老师的邀请,到该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此期间,我与该院师生们愉快地分享这几年参加中日、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的经历和体验。此后至今,笔者先后十余次赴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音乐学院、牡丹江师范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及内蒙古自治区多个音乐艺术院校参加民族音乐学学术会议,参加博士、硕士研究生答辩和进行其他学术交流活动,与北方地区的同行和师生们就少数民族音乐和跨界族群音乐问题展开了积极的互动和讨论。
(二)东北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比较课题的学术路向分析
要想开展东北与东北亚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以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为代表的人文社科整体学术思维和观念格局的整体把握。若就此梳理一下相关的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向,可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即在其“继往开来”的宏观思考中提出了“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这一学术概念,其中包含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板块”类型,如“北方草原”“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另一种则是“走廊”类型,如“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16]。若比较两者的作用,可见前者作为“民族(音乐)文化板块”虽然已经形成了区域文化研究的规模和景况。而后者作为“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作用,就是用来连接不同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板块,使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兼及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差不多与此同一时期,西方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学者也在民族志定点个案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多点(音乐)民族志,合作民族志以及“主文化、亚文化、交叉文化”的社会文化纵向结构等新的研究观念和设想。[17]如前文所论及的,在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法论中,目前存在着某种(音乐)文化圈、文化层互相交织、嵌合的整体概念。其中的文化层里带有“原生、次生、再生”结构特征。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又与其他学科学者以及政府、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共谋”关系,树立起了“传承、建构和创新”以及“‘非遗’音乐、节庆仪式音乐和创作音乐”等新的“主、亚文化层”学术构架。由此看,在近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也就此形成了一种带有“联横合纵”及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意味的跨世纪转型现象。
(三)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东北、东北亚音乐研究课题
2011年9月16-18日,笔者借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论坛——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机会,与包括东北学者内的各地专家共聚一堂,并做了大会主题发言《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2011年9月24-26日,笔者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参加了该院主办的“交流·合作·发展——东北亚区域跨境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宣读了论文《云南与缅甸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传播与交融二题》。2019年12月26-28日,笔者又于8年之后应邀参加了牡丹江师范学院召开的“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学术研讨会”。
东北亚区域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合影(2019年12月27日)
2011年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论坛——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按参会论文的研究对象,将所有议题划分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中国藏、维、汉诸族与南亚、中亚、东亚地区和中国东北、内蒙古与东北亚地区等几个基本的学术板块,其中的后一个板块里,包含了涉及东北跨界族群音乐的如下几篇学术论文:刘桂腾的《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通古斯萨满鼓——以“流域”为视角的跨界族群萨满音乐研究》、张翼善的《朝鲜民族长短的特性研究》、宁颖的《跨界族群语境中的“盘索里”表演——中国延边与韩国传统说唱音乐表演的历时性比较研究》和李然的《解读中俄跨界民族(赫哲-那乃)萨满教仪式音声的现代变迁》。另外,该会还专门设立了“研究现状综述与分析”板块,其中包含了李然的《中俄跨界民族(赫哲—那乃)音乐研究情况综述》和宁颖的《朝鲜民族传统音乐之“跨界”研究述略》两篇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相关的力作。仅从这些论文的内容加以分析,可以捕捉到由此至今近十年来的几个发展趋向:其一,刘桂腾的文章采用了以“流域”连通板块的视角,张翼善和宁颖的两篇论文以中韩音乐为对象,均带有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横向比较研究的思路;其二,从几篇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如萨满教、萨满鼓、朝鲜族长短、“盘索里”表演以及东北亚佛教音乐看,已然包含了“原生、次生、再生”诸纵向的社会音乐文化演生层面。换言之,我们所期待的一种带有“联横合纵”及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意味的跨世纪转型现象,在该次会议中东北亚音乐研究板块的议题里已经得到了明确的体现。而在该次会议的跨界蒙古族音乐比较课题和黑龙江省的另外几次跨界族群音乐学术研讨会上,这类学术选题和研究方向也都已经包含在内。
四、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研究生的相关研究课题
通过新世纪以来自己参加和参与举办的一系列相关学术会议,我们先后涉及了东北和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中各种不同的课题研究方向,其中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以满族和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民俗音乐及萨满音乐、乐器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领域里,已经发展出了以萨满乐器和中俄传统音乐为主要对象的跨界(境)比较研究学术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以往学界有关本地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课题里,一直比较重视以族性与音乐特征分析为主要对象的个案研究和跨省区的相关比较研究。在包括了“原生、次生、再生”诸社会音乐文化演生层面的整体音乐文化系统中,这类研究主要涉及相对“原生”的层面。相比而言,以往学界对于传统仪式音乐(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仪式音乐)、旅游音乐和节庆仪式音乐等带有“次生、再生”文化特征的另外两个层面涉及较少。而从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方面来看,近年来的学术成果也主要是集中于传统萨满乐器的跨界传播以及两地原生音乐文化风格特征的异地比较分析;对于因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文化涵化与交融以及因不同国别政治、宗教、社会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在“次生、再生文化层”发生的音乐文化变异、变迁及族群、文化认同等问题的关注还不多见。对此,我们在指导研究生进行与北方少数民族及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相关的研究课题时,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力度。
二十年来,我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指导的涉及东北、内蒙古等北方民族音乐课题内容的学位论文计有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1篇。以其中涉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的两篇博士论文为例,一篇是宁颖的《中韩跨界语境中延边朝鲜族“盘索里”溯源与变迁研究》(2014),可将其内容和主旨归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作者将坚持数年之久的,以延边朝鲜族盘索里为对象的考察研究与中韩盘索里的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结合起来,体现了由定点个案到多点(线索)、比较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发展轨迹。第二,该文通过对中、韩“盘索里”由古至今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行了全方位溯源,追述了其产生、发展、繁荣、衰落至复兴的一般轨迹,将历史民族音乐学引入中韩跨界族群比较研究课题,隐现了共时性到历时性研究的另一条发展轨迹。第三,在立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文化中的音乐”研究观念,深入地讨论、释读盘索里表演过程中族群与个人身份认同建构要素的同时,还通过对韩国盘索里音乐的认真学习,弄懂、说清了该类音乐的形态机制特点,为以上针对对象主体及主位意识的文化释读奠定了同对象客体相关且作为客位描写对象的艺术与物质基础。从宁颖文章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以中韩朝鲜民族的原生音乐文化(原生层),东亚汉字与佛教文化圈音乐文化(次生层)和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播与变迁(再生层)三个基本的文化演生层次,集中展现了作者关于此方面研究课题所拥有的较突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
另一篇是张林的《建构的传统——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2017),亦可列举其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张林文拥有站立在新颖、前沿的学科方位,紧密结合音乐现实与实践的学术视角。作者写作伊始便面临的一个挑战,即怎样处理和对待满族音乐,尤其是萨满音乐文化的“本真性”与“象征性”的关系,以及是否在自己的研究中代入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不同研究观念等问题。为此,他选择了“加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借用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历史民族音乐学以及仪式音乐民族志相关理论和方法,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相关对象进行分析,对满族音乐这一领域的研究缺失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他在文中使用了“文化建构”“重新建构”和“文化认同”这样的关键词,带动了全文的学术主旨和研究思路,由此一定程度走出了以往较习惯于仅在“非遗”“传承”和“发展”“创新”等概念维系之下展开讨论的学术研究旧舀。第二,作为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课题,张文通过由微观、中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的多层次把握,完成并体现了由音乐民族志田野实践到音乐人类学理论的探索和升华过程。张文立足于微观个案研究,通过对现存的新宾满族传统仪式有民间丧葬仪式、萨满仪式、正月扭秧歌放路灯“撵鬼”习俗、满族传统婚礼习俗、清皇故里祭祖大典以及清永陵祭祀大典等对象内容所做的田野考察,做到了对微观研究对象的“穷尽”。同时,张文还意图超越新宾这一地域性文化范围,从同样具有“建构”意味的“满族文化研究”这一区域性、“民族性”中观文化层面,“对当今满族与满族音乐的内涵进行分析,指出其具有鲜明的建构特点”。作者“利用文化层的研究方法对新宾满族音乐进行划分并分析,从中找出音乐与认同接通的途径”,设立了有关音乐民族志文本建构,结构与音乐风格分析,音乐认同、认同差序分析和解释“英雄圣祖历史心性”等具体、有序的分析步骤。此外,张文仍然结合“满族音乐”这个充满了建构或重构意味的、特定的研究对象,从宏观的音乐文化学和符号学角度,讨论了“符号的两种不同层次的意义”:“作为增大涵义系统的新宾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和“作为增大元语言系统的新宾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同时对“音乐如何体现认同”“传统or伪传统?”“‘建构的传统’的历史视角”“文化建构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其三,张林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目前所做的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方法论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后来的几篇采用相似研究方法的博士论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其中,张林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刊登的“音乐与认同”专栏(2017年第2期)和《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刊登的“建构与认同”专栏(2020年第1、2期)两个专题中发表的两篇论文,对于该类学科方法论建设有着直接的贡献。
说起这些学生们的学位论文,不由得再次勾连起自己对30年来在这一领域所经受的种种学术磨炼怀有的一点感恩之心!从指导这些论文写作的结果看,我在那些颇为艰难的思考与探索、纠缠与磨合过程中所积累的研究经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铸就的、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文化整体观和方法论思维,让我在把握宁颖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和张林的满汉文化比较融合研究等选题时有了底气;而我在东北和韩国的多次田野考察经历,从最早对新宾满族歌舞音乐的那次考察到后来对韩国传统仪式活动的多次参与,则在我与张林和宁颖切磋研究策略和论文布局时派上了用场。同样的例子,还有在指导李博丹的硕士论文《中国朝鲜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地域性比较研究——以哈尔滨、鹤岗、桦椿村三地主日仪式的比较为例》(2009)时,便融入了自己长年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和韩国基督教音乐的体验。而我与红梅、苗金海等博士研究生一起考察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文化的多次经历,也在指导相关博士论文,如红梅的《当代蒙古族敖包祭祀音乐研究——以呼伦贝尔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为例》(2011)、魏琳琳的《“走西口”语境下的民间音乐城市化——以内蒙古二人台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为例》(2013)、李红梅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乐考察与研究》(2014)、苗金海的《敖包祭祀场域下鄂温克族音乐文化的建构与认同》(2019)以及哈斯巴特尔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卫拉特蒙古族呼麦、冒顿·潮尔及其音乐研究》(2018)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此外,这些年来还参加了东北和内蒙古许多音乐艺术院校的博士、硕士论文的评审、答辩工作,也同样倚助于上述那些田野考察和研究经历。这些后述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本文所讨论的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目标相近,意义相符,但限于本文篇幅,拟留待将来再找机会予以继续讨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一般项目《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理论建设和选点、比较研究》(项目号:20BD068)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载于《北方音乐》2022年第1期(改版首刊号),引用请据原文。
注释:
[1]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8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再版。
[2]杨民康:《中国民间歌舞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初版,2019年修订版。
[3]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4]杨民康:《论云南少数民族南传佛教的乐器、器乐音乐及其与原始佛教音乐的渊源关系》,《2000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音乐2),财团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编,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71-402页。
[5]杨民康:《论佛教传播史晚期的音乐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乐的比较》,《普门学报》2003年第17期。
[6]中西和夫:《日本净土教仪礼的音乐特性》,《2000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音乐2》,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3-196页。
[7]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记》,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
[8]洪润植:《韩国之佛教仪式与佛教音乐》,载《2000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音乐2》,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25-236页。
[9]杨民康:《论佛教传播史晚期的音乐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乐的比较》,台北:《普门学报》2003年第17期。
[10]杨民康:《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载袁静芳主编《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11]杨民康:《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载袁静芳主编《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12]杨民康:《唐代〈骠国乐〉中的十二首佛曲及舞蹈内容解析》,台湾:《普门学报》2008年第43期。
[13]参见杨民康《缅甸僧侣剃度仪式的乐队走街及其音乐历史溯源》,《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6期。
[14]参见[韩]朴范薰:《梵呗东渐及其韩国化》,载袁静芳主编《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23页。[韩]权五圣,申玉粉译:《韩国佛教音乐研究的现况及课题》,载袁静芳主编《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9页。
[15][韩]全仁平:《韩国与西藏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载袁静芳主编《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41页。
[16]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载四川大学《“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转引自中国知网),2003年。
[17]Timothy Rice:“Time,Place,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Ethnomusicology,2003,47(2),pp.15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