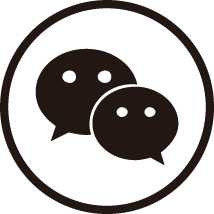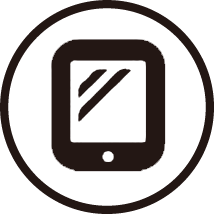严肃音乐的创造者、演绎者和欣赏者需要评论或评论者吗?又是否受其影响?这个问题得具体分析。比如早些时候的作曲家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媒体和批评界追踪,能心无旁骛地创作,缘故是那时尚无“音乐评论”职业。
同样,文学批评也出现得很晚。直到歌德的时代,即18至19世纪之交,这位名作家开始抱怨记者和评论者的指摘了。歌德认为批评是个天真的举措,它未将艺术创作的自发性加以考量——这一特性在莎士比亚时代还不受非议,堪称创作的法宝,如今却被以理性眼光分析和批判,无疑是“反艺术”的。
一个看法和观点的提出,多少带有主观性,特别在与切身利益相关时更是如此,歌德对文艺批评“反批评”的一家之言,就是这样。然而,文艺批评本身的主观性如何?事实表明,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极富主观色彩且观点无法被严格证实。人们可自由论说、凭热情与好恶将主张完满表达,但像数学家用方程式、物理学家用力学定律或法官以律条来印证其观点,是艺术评论家办不到的——只因艺术的标准难以界定。
艺术可说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以音乐为例,启蒙运动以前,教会和贵族有着对音乐作品的绝对评判和取向,他们的要求和品位就是“标准”,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创作者要据此来写作,以求得安身立命之基。只因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教堂和王室是艺术家的惟一资助者,其作用十分凸显。例证不胜枚举,比如海顿因有主可依,在宫廷度过三十年衣食优渥的光阴,但孑然无依的莫扎特只能在维也纳只身闯荡、艰难过活;巴赫曾受雇于教堂和贵族领主,当某地不再适合生存,他也未想过独立,而是忍受煎熬、坐等外地的一纸聘书——有着众多子女的巴赫不敢冒自立门户的风险。因而教会和贵族给了艺术家生活保障,这是首先应被肯定的。诚然他们的“标准”有时也限制了天才的发挥,这是时代局限性,原也无可厚非。
后来,人文主义思潮颠覆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创作模式。启蒙运动带动了“第三方”,即上述甲乙方之外的另一广大市民阶层——听众的兴起。逐渐地,音乐作品的创制不再为一两个人的要求所左右,而是向剧院、音乐厅里无可计数的普通听众靠拢。音乐家也渐趋脱离被动的环境,成为一个个独立创作者,这里的第一人当属莫扎特,其后是(退休后的)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由此,听众的评判成为艺术标准,特别在维也纳,音乐好不好,大伙说了算。来自听众阶层、代表听众发声的职业评论者,大概于此时出现。他们的存在犹如民众在艺术领域的律师。
评论者试图将个人和大众的感受进行统一,将其系统化、条理化,为受众者说明和阐释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判断其作品的优劣处和价值并给予其一定理由,形成文字置于公共空间。作为职业化群体的批评者,通常代表了前卫、时髦的意见,并以专业素养来针对普通公众的唯唯诺诺甚至对艺术品之麻木态度。但有的早期评论不甚公允,比如面对里程碑式的大作,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由于尚不了解而微词甚多,后被证实批评有误;还有些别有用心的知名评论家,因派别之争站在一方故意歪曲另一方,对对方作品的真价值视而不见,如维也纳音乐美学家E.汉斯立克针对瓦格纳、李斯特、布鲁克纳音乐作品的攻击文字。不能拿这些极端情况以偏概全,认为评论都是如此。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评论确有优劣之别。已故法裔美籍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认为,“评论的优劣取决于评论者对我所走过的这片风景的了解度。如一批评家将我正上演的作品烂熟于心,对我说‘这样不行!我清楚你本要达成那样的效果,却没有办到’,并给予我充足的理由。这样的意见我侧耳恭听。因为只有真熟悉该风景的人才了解个中奥秘。但谁要只是个旁观者,谁只看过这风景的二维照片或画像却未践行其中,那他无权对艺术家指手画脚。”确是一语中的。“人们在阅读一篇评论的伊始,已能感知到这一点——评论像是用指尖直接触碰伤口那样敏感和精准!”马泽尔如是说。
可见,评论有好坏正误之分,也有针对作品与针对演绎之别。有外国学者指出,19与20世纪音乐评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面向新创作的音乐,即对值得永久聆听的作品进行去留梳理;而后者针对新的演绎,即为听众遴选出哪些表演(包括现场和唱片录音)值得永久纪念。中肯的评论虽说像优秀作品那样“难出炉”,并不意味这东西不存在或很少。音乐评论约两百年间的历史上,优秀批评者层出不穷,其本人很多就是大音乐家,如柏辽兹、舒曼、瓦格纳等人,他们对音乐创作了如指掌,对艺术的评判无疑是敏感而卓绝的;后来的罗曼·罗兰、萧伯纳等人都是在文豪队伍中最通晓音乐者,他们的乐评文字流传至今;进入20世纪,配合信息和媒体的传播“加速度”,唱片、广播、电视、网络等新收听形式的屡屡翻新,让音乐前所未有地普及,与之伴生的世界各地的音乐批评、评论者无可计数,音乐评论形成传统与习常。
音乐艺术由原创者、二次创造者和接受方三方面构成。二次创造即表演,有别于文学和美术作品,接受方可直接欣赏创作,只有简单的二元关系。聆听音乐却需要一个或若干个“中间人”,即独奏或合奏者,他们须将乐谱转化为听得见的声音。因而,音乐评论的功能也就分别面临着这三种人。对三者的影响到底如何?通观评论史,可说乐评对原创者的地位和声望有过影响但对创作本身作用不大,因为评论是产生在创作之后,且作曲者自有一套写作规律和习惯,不管评论意见中肯与否,都很难融入其今后的创作中去。只能说在“抑扬”和宣传方面,如上段提及的遴选作品或推举新人上起过作用——舒曼以他特有的敏锐,在乐评中最早向公众介绍了肖邦和勃拉姆斯的天才,这对二位的职业发展,特别是肖邦作品在德国的普及曾起到辅助作用。
评论对从事二次创造的演绎者及其表演本身,影响要大一些。正如马泽尔总结的那样,演绎未达到某种效果或意图而被内行点破,在后续表演中有精进完善之可能;表演队伍里的“新晋者”也许因为乐评的宣传让公众认识自身,在风格上扬长避短、迎合舞台,但总体来说这影响还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小提琴大师平夏斯·祖克曼断言“即便最专业的评论对我无多大帮助”。祖克曼也许不需要评论,但是否别人需要?这就引出了评论针对的第三方——艺术接受者的问题了。
作为普通人的绝大多数听众,并非专家也未受过专门的训练,在面对大量音乐表演知识、专业术语及其创作背景时,总会无所适从,这时若有人在节目单上做个必要导赏,演出后再为表演作适当点评,那么听众在一前一后就有了“倚仗”,无疑更有助于欣赏并理解艺术。这与文评、书评、影评等其他文艺评论功能相似。
参照评论,与自己的切实感受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检验聆听质量,久之,鉴赏能力会得到提升。乐评者推荐或不推荐的演出和录音,假使意见每每中肯,会在听众心中形成指南和律条般的权威。那么即便错过某场演出,也能在事后通过文字了解,或据此决定是否去购买唱片或观看相关场次。目前的惯例,是很多重要演出都有连续上演至少两次的安排,歌剧则更多。如按上述办法,既节省开支又节约了时间,只因有评论家为我们把关。可见,评论对第三方的作用非常可观,可说其主要的作用对象是艺术接受方。
音乐批评的立足点是专业素养、积累和洞察力,以乐谱和现存演出资料如CD、LP、DVD等为依据,使评论对象明朗化的同时进行合理类比、谈古论今。如再拥有一支流畅自然的文笔,形成雅俗共赏的文字,必将影响更多的听众乃至音乐从业者。正因音乐评论代表公众发表意见的性质,故此它至少是由理性思维主导,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深入浅出的读物。尤其在信息如此爆炸、面对海量资源手足无措的时代,从中挑选艺术精品、节约你我的时间更显可贵,这需有人深耕其中,发掘并分享之。因而,今天对合格评论者的需求也许超过了任何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