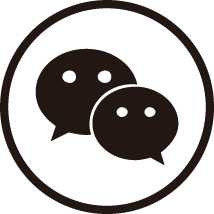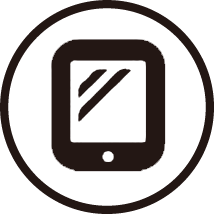当科普兰进入中国在美国的音乐界,无人不知这位泰斗级的人物,而登陆中国,他也算占得先机。凭借一本《怎样欣赏音乐》的普及读物,科普兰的名字早在1984年就为国内爱好者所知晓。那本不足200页的小书,通过音乐要素与结构的分析,普及了音乐欣赏的基础知识,但深入浅出有时只是一个愿望,很多人读到难点就搁置一旁了。尴尬的在于,当这本只卖0.78元的书摆在书店时,古典音乐的市场尚未在中国打开。书里提到的作曲家,很多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怎样欣赏音乐》,[美]艾伦·科普兰,丁少良/ 叶琼芳 [校],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
虽然当时的收音机开播了调频立体声,但播出的音乐十分有限。除了贝多芬、柴科夫斯基、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人的作品,美国作曲家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就连激光唱片也是1985年在北京国际图书音像博览会上才正式亮相,能有进口磁带就算稀罕物了。等我们陆续把激光唱片摆放到架子上,也是基本曲目配齐了才想到美国作曲家。于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出品的科普兰的作品(他自己指挥)才有了一席之地。人们才知道,写了《阿巴拉契亚之春》《小伙子比利》《墨西哥沙龙》的那个人还会指挥,还是个教师和音乐批评家。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还写了其他什么。直到这本装帧漂亮的《科普兰论音乐》拿在手上,才知道他老人家的道行有多深。
比起一辈子就待在一两个地方的作曲家,科普兰可谓见多识广。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巴黎跟布朗热学习作曲,二战结束后又去意大利游学,布列兹那帮小青年搞的音乐实验他也兴趣盎然。美国大萧条时期,他剑走偏锋去了拉丁美洲,发现了查韦斯、维拉-罗伯斯这些风格迥异的南美作曲家。而作为最有代表性的美国本土作曲家,他还看到从序列音乐到爵士乐之间的广阔天地。无论斯特拉文斯基、还是维也纳新三人团的勋伯格、韦伯恩和贝尔格,乃至于美国的格什温无不通晓。功成名就时又去推动后学,慧眼识人,扶持了不计其数的年轻作曲家。在伯恩斯坦刚出道就看到这是个美国本土的通才(演奏家、指挥家、作曲家),一眼就看出伯恩斯坦是欧洲古典音乐传统和爵士乐完美结合的最高典范。不仅笔耕不辍,还做讲演,开课堂,尽心尽力地做音乐推广。不夸张地说,一本200多页的小书,20世纪的古典音乐的方方面面都没能逃脱他的眼界。
从柏辽兹到李斯特虽然20世纪之前的作曲家大多不在本书所论之列,但对20世纪音乐发展有推动、有创见的作曲家,科普兰岂能放过?不出手则已,点到就是要害。像评价柏辽兹,谁都绕不开《幻想交响曲》,他独独看中《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若不是精通作曲专业且独具只眼,谁能看出这个作品竟然影响了十几位后来的作曲家,成为理查·施特劳斯、马勒、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穆索尔斯基、格里格、斯美塔那、威尔第、柴科夫斯基、圣桑、弗朗克和弗雷的创作密码。
科普兰指出,这首中提琴与乐队的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作曲家并非围绕这件乐器创作协奏曲,而是让独奏转化为不可或缺的助奏角色,这种做法史无前例”。在西方音乐史的读本中,也少见这样细致入微的独特观点。读到这里豁然开朗。理查·施特劳斯的《唐吉坷德》里的大提琴的运用,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修道院里僧房的音乐对比“哈罗尔德”的第二乐章,钥匙都在这里。连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听着柏辽兹长大的,马斯奈、弗雷也是竞相模仿柏辽兹的艺术歌曲,甚至勋伯格的写作也借鉴了《浮士德的沉沦》里“招魂”的场景音乐。
在马勒、奥涅格和梅西安的有些作品中,柏辽兹音乐中“高贵的爱”和戏剧性的虔诚,亦如月映水中。甚至在音色组合方面也是前无古人,比如巴赫与莫扎特的笔下的长笛和低音管乐,到了柏辽兹手里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音色对比。柏辽兹“能够针对不同的乐器找到其最佳的音域范围,并在这个范围内写作”,同时他又十分关注乐器之间的组合,而不是把各个声部不相干地摆在一起。如此敏锐的感觉,扎实的功底,同行里也只有高人才能有这样的眼光。
另一位花费笔墨的要属李斯特,那篇文章的题目居然是“先驱李斯特”。一个“先驱”,道出了李斯特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曲家的意义。对于同时代的肖邦、舒曼对李斯特“哗众取宠”的指责,科普兰并不否认。接着笔锋一转,说李斯特比他们二位多活了二十多年,恰恰在这个时期,他在钢琴写作上大放异彩。《叹息》中,他把钢琴当做竖琴,《第十一号匈牙利狂想曲》钢琴又变成了钦巴龙(一种匈牙利本土乐器),在《死之舞》里,钢琴简直是铜管乐和打击乐,嚣张起来,钢琴犹如一支管弦乐队。这些对钢琴性能的开发无不是李斯特无可比拟的创造。正是作为演奏家,才使得这些作品直接在钢琴上诞生而非书桌上。
李斯特笔下的“音乐质感”“声响织体”和“简化伴奏声部”,让一串串闪闪发光的和弦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没有李斯特的精巧设计,“不会有德彪西或者拉威尔充满魅力的音乐织体,也不会有斯克里亚宾柔情的诗意”。这种穿透性的眼光带有职业的敏感和历史观的通达。这还不算完。除了立意新颖、构思独特,李斯特在和声方面的思考同样出色。
这点德彪西在他的音乐美学文字中也有提及。往好听里说是李斯特对瓦格纳在和声进程方面大有影响,若按照德彪西的说法,瓦格纳简直就是抄袭,只是李斯特待人宽厚,一笑置之。 李斯特还是印象派的先驱。他有一组钢琴曲(12首)从未演出过。其中的《圣诞树》、《夜钟》在听感上和早期德彪西极为接近。新奇的和声进程、出人意料的转调虽然出于本能,但在手段上完全是现代派的。受其“恩泽”的还有挪威的格里格、俄罗斯的斯克里亚宾和穆索尔斯基等一干人。
超越同时代的评论家现代作曲家的杰作自然逃不过科普兰的金睛火眼。韦伯恩的《五首乐队小品》中最长的也不过几分钟,“但似乎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丰富的意涵”,令人窒息,甚至喘不过气来。本质天真的贝尔格和他的老师勋伯格完全不同,他显现了一种“温暖的、感性的,特里斯坦式的个性”。对巴托克《钢琴奏鸣曲》的评价是:“锋利、有穿透性的节奏,强硬而冷静的质感”。双刃剑在于,如此鲜明的个性往往容易过多自我重复,这是一种危险,而巴托克的高明就在于“仅在危险的边缘游戏”。这样贴切的比喻真是妙不可言。可惜巴托克不一定能够听到。当然,谨慎如巴托克,既便听到也就是莞尔一笑。
斯特拉文斯基最为科普兰所看中,花费的心思也最多,称他是这个时代中一个“最独特、最有个性的作曲家 ”。他举例说明,我们在聆听时也容易产生的错觉。当我们不留意地听某个乐曲,会把风格相似的作曲家混为一谈。偶尔会把莫扎特混成海顿,或者把巴赫和亨德尔搅在一起。有时也把拉威尔当成德彪西。但是科普兰“从没有被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诓骗过”,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才会写出那样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科普兰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论是一段旋律、一个和弦,音符总能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面对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看到了音色,萨蒂看到了现代音乐的解放者,肖斯塔科维奇看到“灵魂的扭曲和道德的放弃”,更多的人则为他那癫狂而不规则的节奏所震撼。但科普兰却看中斯特拉文斯基述说音乐的“语音语调”,略显严肃、一本正经的标志性音乐表情,以及非学院派的织体表达。这三点构成他创作的核心。在经历了早期三部芭蕾舞剧的狂暴之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的关键词成了“清醒节制”。
正当巴黎的观众期待他更出位地重登舞台时,三幕宗教清唱剧《俄狄浦斯王》却是严肃礼服着装的男声合唱和收敛的管弦乐配器。让人大跌眼镜。然而科普兰却看到从《彼得鲁什卡》到《俄狄浦斯王》之间的联系,从原始仪式到个人悲剧,从客观元素的表达到抛弃现实主义,特别是《管乐交响曲》《八重奏》,斯特拉文斯基在向着“回归巴赫”的路上逆行而上。殊不知,这种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和其他艺术领域的变化是相互勾连的。在毕加索同期的绘画、艾略特的诗行,和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中,这种不带个人色彩的美学理想的回归,让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者不谋而合。当此时刻,这样的视角早已超出了一个同行的评判,应该说,是跳出古典音乐之外得出的结论。反观同时代的欧洲、美国,具有科普兰这样的艺术修养的人凤毛麟角。
如果只读过《怎样欣赏音乐》(新译本书名为《怎样听懂音乐》),那你只领略到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的科普兰。而且那本书也不是随便可以“普及”的。当你读了《科普兰论音乐》,才知道他的学养之深厚,见地之敏锐,且行文朴实又不失精准。套用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轻看了李斯特》,不读此书,也许你我会轻看了科普兰。
↑↑↑点击上方图片可以直达
关键词: 中国音乐教育 中国音乐教育网 CSMES 音乐教育 中小学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投资 音乐投资 中音联投资 才艺擂台赛 音乐培训 钢琴 中音联新文旅一带一路艺术小镇 C.CMU艺术小镇 中音联邮箱csmes@126.com